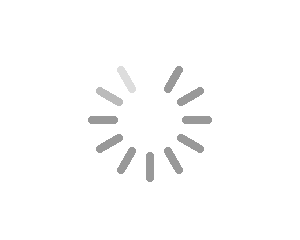至于跑现场的价值,一句话,对于人文古树,人文森林,没有现场,就没有文学,也没有学术。我的人文古树和人文森林的文章,都是这样。譬如,三门峡的那棵树,就是那棵七里古槐。那个地方在龙海线上,地名叫七里镇,那次我本来是去河南开一个经济会议,开幕式结束以后,因为我在新闻界多年,当地报社的朋友都来看我,我就问你们这里有什么树?他们说,有七里古槐,我听成了“稀里古怪”。我说怎么个怪?他们说带你去看看你就知道了。去了,一看,还真古怪。第一眼的感觉是,树上怎么长了那么多大个疙瘩?一个疙瘩,脸盆这么大,疙里疙瘩,你踩着就能爬上去树。感觉这不是我们通常的树的概念。我有些震惊,自己当时还画了一幅画。这是我第一次用国画画树。我的第一感觉就是,这是一个苦难的象征。河南这个地方就是中国苦难的缩影。蝗灾、水灾、旱灾、战火、兵燹,中国人在那里苦透了,才产生这么一棵树。杜甫写三吏三别在那里,安思之乱在那里,日本人屠杀也在那里,不管经受多少磨难,这棵树都没有倒掉。所以我就写了那棵树。没有现场,就感受不到那么多的内涵,绝对写不出来。当然,别人去了,可能也会写这棵树,但应该不会这么写。文学是形象思维,个性艺术。
说起来,这几年里,我访古树,跑森林,在中国也算走了几个“万里长征”,跑得两个腿已经不行了,关节老了,可能再也跑不动了。人文森林,一路走过来,这可能也就是我的高峰了。
梁衡人文森林作品示意图
原载于《树梢上的中国》(商务印书馆出版)
红色题材的历史揭示与绿色题材的现实抒写
李景平:您散文创作形成两大系列:红色题材散文,绿色题材散文,这恰好契合了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两条道路:红色道路,绿色道路,红色道路通向绿色道路,绿色道路承接红色道路。红色和绿色在你身上是非常明显的标志。您自己也说,古树意象是您“红”和“绿”的聚合归一。这种写作契合,是怎样实现历史发展和写作选择审美融合的?
梁衡:这个问题,从中国现当代道路看,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道路问题,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走向问题;从个人成长道路看,是作为一个作家的自然成长、自然发展过程,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、社会担当历程。
就中国革命道路而言,中国革命走的是解放人民大众的道路。为人民服务,是古今中外人类社会从未提过的宗旨。中国革命就是要解决为人民服务的问题,消灭剥削和压迫,让人民大众有饭吃,吃饱饭。这是中国革命的红色道路。中国革命胜利了,进入中国建设的时代,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,我们解决了人民大众有饭吃吃饱饭的问题,却遇到了能不能吃好饭持续吃的问题,我们的后代能不能吃好饭持续吃的问题,所以,中国提出可持续发展,提出生态文明建设,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。这就是中国建设的绿色道路了。当代中国提出两个共同体理念,一个是人类是命运共同体,实际是人类和平共处的问题;一个是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,实际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,也就是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。这是新的时代命题,是红色道路和绿色道路融合在了一起。
就我个人经历而言,因为我出生和成长在一个革命干部家庭,从小受到的是红色家庭教育;读大学读的是中国人民大学,人称“小党校”,读书接受的是党的传统教育。我们那个年代,学生大学毕业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,要做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青年,这自然是继承了红色革命传统。应该说,这种继承是流淌在血液里的继承。所以,我的红色散文抒写自然是一种“红色”的继承和体现。因为基因是红色的,不可能不关爱红色。在遇到生态环境问题的时候,正好也与自己自小就有的绿色情结吻合。作为记者作家,作为知识分子,甚至作为官员,你的责任、使命和担当,就表现为一种绿色人文情怀和绿色人文关怀。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关怀,是绿色情结(环境状态)的延续,也是红色情结(社会责任)的延续,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、使命和担当的延续。
当然,我写红色文化、红色文学,或者绿色文化、绿色文学,实际上并非一种粉饰,而是一种对传统历史的反思和对社会现实的反思。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后,发展了许多,也进步了许多,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,思想上的混乱,政治上的腐败,作风上的倒退,社会上的芜杂,环境上的污染、生态上的破坏。可以说,我的所有文章,无论红色散文还是绿色散文,其实多是有靶子的,是有针对性的,针对现实存在的现象和问题进行反思。反观我们走过的历史,打捞沉淀在历史底下的细节,发掘湮没于历史风尘的故事,再现消失在历史进程的人物,在人的故事里,树的故事里,真实而生动地将我所发现的一切,以文学审美的形式,呈现于我们的现实,形成历史与现实的对比,形成历史对现实的启示,进而重新竖起一个历史标高,使现实借鉴历史。
应该说,我的人文古树是以古树意象把红和绿凝聚在了一起,呈现为一种具象的、审美的、文学的表达。这应该就是你说的,两大系列散文,恰好与中国革命的红色历史、现代文明的绿色思想吻合在了一起。本质上这源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和现实忧患,是红色继承与绿色担当的文学化。
李景平:您的生态散文多写山水森林,重在挖掘自然之美,或者从自然之美中感悟人类之美,以作用于人们的审美;您的政治散文多写人物,重在挖掘人物的形象之美,在形象之美中揭示人格之美,以直捣人们的心灵。这两种书写可以说展现了一种世界大美和人间大美,是一种大审美大境界的文学书写。请谈谈您在这种审美创造和文学构建上的“秘诀”。
梁衡:我的散文的色彩,其实是交织融合在一起的,红中有绿,绿里有红,好的文学审美总是浑然一体的。
我的绿色散文、生态散文,过去叫它是山水散文,是作为风景来写的,现在叫它是人文森林,则是作为人文生态来写的,但风景和生态里,实际不是纯粹的自然风景和自然生态,而是有人、有社会、有精神,也有红色。
我的红色散文、政治散文,或者叫历史散文,或者叫人物散文,是作为政治来写的,是作为人物来写的,也是作为历史来写的,但政治里有自然,人物里有生态,历史里也有现实,而在历史、政治、人物里,也有绿色。
生态散文乃至生态文学,其实不应该仅仅是纯粹的自然生态的表现,而是自然生态、社会生态、人的精神生态的一种审美混合。没有这样的生态内涵和生态外延,怎么可能是完整的生态文学?所以,我的笔触从自然生态伸向人文生态,也从人文生态伸向自然生态,要打通生态的灵性。
所以,我主张写大事、大情、大理,这也是我的文学宣言或散文理论。文学为思想而写,文学为美而作。对于散文之美,我过去讲,体现在三个层次:形象美(描写美),情感美,理性美。没有形象上的美、情感上的美、理性上的美,怎么呈现大美,怎么呈现人的精神之美和人格之美?对于生态散文,现在讲,要延伸三个层次:自然美,生态美,文化美。我曾给散文写作概括了“五诀”:形、事、情、理、典。这“五诀”,基本把大事、大情、大理、大美、大形象概括进去了。当然,生态文学,一草一叶都关情,完全可以小处见大的。
这样,文学的“大美大爱”意境就出来了,人物的“大写特写”形象就立起来了。瞿秋白,追求革命,不惜春华,从容就义,非常坦然,最后连自己的缺点都要说出来了,多么伟大的人格?周恩来,淡泊名利,无儿无女,大无大有,最后连骨灰都撒向了大海,多么广阔的胸怀?张闻天,曾经显赫,终至沉默,被埋没沉寂多年,也曾遭遇批判,但终生坚信革命,多么坚韧的精神?我的《晋祠》《夏感》《青山不老》《壶口瀑布》《觅渡觅渡渡何处》《跨越百年的美丽》等60多篇次散文被选入教材,大概就因如此。
李景平:您提出过一个创作观点:“用文学翻译政治。”您的红色散文写中国革命,是以政治视角,聚焦政治题材,凸写政治人物,彰显政治意义。生态文明作为绿色革命无疑也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另一种革命。您的绿色散文书写,是否会聚焦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时代的典型人物?
梁衡:其实,我的多篇散文,无论是山水散文、人文古树,还是政治散文、人物散文,也都写到了绿色人物。《青山不老》《看见绿就想起你》《杜寿鹏要堵贺兰山阙》都写的是绿色人物。至于生态文明时代的绿色人物,我肯定会关注,但觉得不会马上就去写。
因为我现在是以一个作家在写作,不是记者,记者写的是现在的事情,是新闻的事情,这不是作家做的事。作家写的是历史沉淀的东西,故事也好,人物也好,不是作为新闻报道来写,而是作为思想来写,作为是艺术来写。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。通常说,新闻结束的地方,就是文学开始的地方,但新闻结束后的文学开始,是需要时间沉淀的。即使是人物,也要沉淀。在新闻结束的地方里沉淀出经典的东西,普遍经历的事情中沉淀出典型的东西,没意味的现象中沉淀出意味的东西,才能凸显一种审美,也才能成为文学的形象。入选小学课本的《青山不老》就是典型的由新闻到文学的沉淀之作、过滤之作。前后已有40年。
要写的话,山西植树人物刘清泉可以写。这老先生一辈子植树,是山西有名的“植树书记”,当了林业厅长,到了县里,就召集常委会,开会干什么?一人给发一个纸条,考考你的林业知识。退休以后,背着个照相机,跋山涉水寻找古树,最后编辑出版了《山西古稀树木》,是个很有意思的人。黑龙江一个书记也可以写。这个书记,在林区看见一棵树被折断一枝,突然喊停车,司机突然踩刹车,不知道什么意思,车上的人急忙跟着下来。他说,谁把树毁了?要所有的人脱帽,对着那棵树致哀。这就属于很有个性的那种,我内心热爱这个细节。人文森林和生态文学的写作,要的就是这样的细节和氛围。
不过,有些故事,有些细节,我不会写。你刚才说到山西武乡的“红星杨”,说是朱德栽的“红星杨”,掰开树枝,里面是一颗红五角星,是很奇,很有意思。我第一次见,是在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办公室。他从山西回来,带回一把“红星杨”树枝,掰给我看,说你也回去看看。后来我去过,也曾经想写,找了好多八路军的史料,但最后没有写成。为什么没写成?因为这是个巧合,我后来发现“红星杨”不光武乡有,别的地方也有,就是那个树种。当然,作为文学,把它演绎成八路军鲜血染红了它也可以,但显得牵强。
说实际,人文森林创作,我一个人一棵树一棵树地找,一棵树一棵树地写,比原来想象的要吃力,如果有一支作家队伍,则会好的。作为学术研究,则需要学术带头人,需要一支力量。如果哪个年轻学者看到人文森林学的价值了,进而作为自己的一种学术自觉,带领一个研究团队来做,我相信,肯定能够做出很大的成就。
(来源:《中国生态文明》杂志2021年第3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