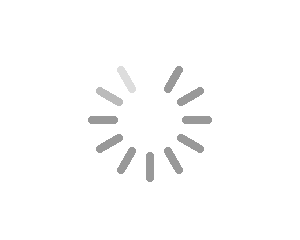人文森林人物学——人对树的尊敬与呵护,典型地体现在林业工作者身上。在自然森林中,树木是具有生态意义的生命;而在人文森学中,树木是具有精神灵性的生命。尊重树木呵护森林的人是代表人类与森林深度交流的人,理应受到社会尊重。人文森林人物学标志性作品有《青山不老》《这里有一座古树养老院》《天山脚下一棵松》《万里长城一红柳》《杜寿鹏要堵贺兰山阙》《徐霞客的丛林》等。在这些作品里,向森林致敬的人们,森林也向他们致敬。这就是人文森林人物学。
人文森林工程学——以古树或森林作为核心,创建人文森林公园或社区,有现实的文旅价值。人文森林观点认为,树的生态会影响人的生态,人文生态也会影响自然生态。过去讲树的覆盖面指树的垂直覆盖,现在应有一种新的覆盖理念:“绿灰比”,看绿(正数)占多少,灰(负数)占多少,看绿灰比例多少。马路面积、墙体面积、汽车数量、玻璃及其辐射面,是灰;绿树面积、草坪面积、水体面积、墙上绿化、房顶绿化面积,是绿。两个数字比,就是城市的绿灰比。按这个理念,乡村打造人文森林公园,城市打造人文森林社区。这方面的代表作有《中华版图柏》《那一片幸存的原始林》《中国枣王》等。
我的人文森林创作和研究,特别强调古树和森林是“有生命的”这个意义。古树与生命同绿,与青史同绿,与人类同绿,人与自然是一种生命共同体。可以说,在地球上,能够与我们人类这样密切进行文化交流而又寿命最长的生命体,恐怕就只有古树了。追寻、挖掘、解读树的生命意义与生态意义,是人文森林创作和人文森林研究的文化核心。
李景平:您的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,是以生态视角生态思维看自然看社会,强调的是人的生态意识,而人文森林的研究或创作,则是以社会视角社会思维看森林看生态,强调的是人的人文意识。两个视角从两个方向指向了人、社会、自然,是融合着看而不是分离地看,是打通了看而不是孤立地看。那么,您的人文森林创作和研究,社会响应程度如何?
梁衡:我的生态文学创作,采写了不少有文化记忆的古树。树木森林是一个传统的散文题材,以前归在山水文学里,现在归在生态文学里。我们称“山水文学”的时候,还没有“生态文学”这个说法,但山水文学其实已经体现了生态文学的内涵。山水文学中所包含的热爱自然、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的思想和美学,不就是现在生态文学的意蕴吗?
当然,我不写纯自然的树,虽然有人写纯自然的树也写得很美很文学,但我不写。就像前面说的,我是调查挖掘树上的历史记忆。所以我称之为“人文森林”“人文森林学”,从文学和学术两方面看,可以认为是生态文化。这就和林业院校讲的“自然森林学”不同,“自然森林学”注重的是树与人的物质关系,人文森林学关注的是树与人的文化关系。
这种文化关系是双重的,既是从自然生态的角度看树看人,也是从人文生态的角度看树看人。这就是,树是自然的树、生态的树,也是社会的树、文化的树;人是社会的人、文化的人,又是自然的人、生态的人。我们从树的身上可以看出人的历史和文化,从人对树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树的生态和历史。所以,研究人类,就要研究与人类发生关系的古树和森林;研究古树和森林,也要研究古树和森林承载的人类的文化和文明。说到底,是要以创作的影响、学术的影响,引起社会的响应,从而获得一种影响社会影响现实的效应。
创作出版。作为生态文学的人文森林,以2012年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一棵怀抱炸弹的老樟树》为标志。从人文森林作品诞生到目前,我已经采访创作31篇人文森林散文,结集出版了五个版本的人文森林文学作品集。2018年由商务印书馆、外文出版社同时出版《树梢上的中国》(中、英文版),香港天地图书公司购买版权出版《树梢上的中国》,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《梁衡人文森林》。商务印书版《树梢上的中国》已印刷四次,脱销,马上出修订本。2018年8月在上海书展开幕首日举行新书发布会,国内媒体报道了《树梢上的中国》出版新闻和作家专访。2018年,《树梢上的中国》被评为商务印书馆当年社科十大好书,并荣登中国出版集团“中版好书”榜。2019年,《树梢上的中国》入围第十四届“文津图书奖”。2020年入选《中国绿色时报》“2019自然好书榜”。2020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,获评生态环境部第一届“公众最喜爱的十本生态环境好书”第一名。
学术研究方面。我2012年在国家林业局提出“树上的文化”概念。2013年在第六届全国生态科学研讨会上发表《重建人与树木的文化关系》,阐述人文森林理论。2013年《中国绿色时报》发消息《建议创立人文森林学实施人文森林工程》。2019年在南京林学院讲授人文森林学,在西南林学院讲授人文森林学,被聘为客座教授,标志着人文森林学进入高校。2021年5月受聘担任国家林草局科普首席人文学者,标志这门学问为官方所接受。到目前,已在全国作了30多场人文森林学讲座。
工程建设方面。2016年5月,“陕北府谷高寒岭人文森林公园”建成剪彩,标志着中国第一个人文森林公园建成,也意味着人文森林工程诞生,成为中国首例因文成景的文旅工程,显示了人文森林生态文学的实际作用。当时《人民日报》专门发文《高寒岭上文成景》来记载此事。
创作“人文森林”散文,创立“人文森林学”,实施“人文森林工程”,意在重建人与森林的文化关系,借森林来保护文化,借文化来保护森林,这是生态文化的细化升华。古树是活的人文博物馆,见证了树的灵魂在历史天空激荡,也见证了人和历史在森林世界闪光。人永远无法脱离自然,人应在尊重自然中追寻可持续发展。
人文森林的现场体验和生态文学的田野调查
李景平:您曾经说过,您原想要写100棵人文古树,但实际写作中每一棵古树,都要做历史研究和田野考古,来回数千里,采访三四遍,耗时好几年,一棵树的写作成本是够大的。那么,在网络信息四通八达的今天,查阅调取资料点击可得,您花费如此功夫写一棵树,实际都要做哪些采风调查、历史研究和田野考证的事情呢?
梁衡:知道我在写人文古树和研究人文森林,国家林草局的同志老给我介绍,说你不是要找树吗?我们这里有树。他们那里是有全国树的档案,200年以上的多少,600年以上的多少,1000年以上的多少,要树有树,要数有数。但这个不是我要的,虽然一棵一棵树都是活的,但没有进入我的人文视野,不合人文标准。所以,我必须到现场,找我要的人文古树和人文森林。
因为是个新学科,必须去做田野调查;因为人文古树是文学写作,而文学是必须要有现场感的。这两条,决定了我的写作和研究,必须到现场去。
现场发现。我如果不去现场,打个电话跟人家要资料,人家不懂你是在干什么。你得去告诉人家我找的这个人文古树是个什么概念。一棵树,当地人最先想到的可能是树的神话传说,我说这个不行。虽然广义上也是一种文化,但不是我要的文化。我要的文化是可以做历史的,必须有真实的历史。这样的树,就很难找。所以,第一次去现场,等于是做个科普,下个订单,告诉人家我要什么树。之后,人家有所发现了,说你再来一趟好吗?第二次去,就看这棵树上发生了什么历史故事,和什么人物发生过关系,然后寻找资料,核查历史,确定内容。第三次去,就要感受体会这个树所附着的历史故事的人文内涵了。核实这些东西,你不到现场,是永远抓不到的。一般一棵树跑三次,都得到现场去发现。
现场挖掘。我们在20世纪20年代引进一个词,外国叫田野调查,考古必须作田野调查。我找人文古树,无论作为文学,还是作为科学,就相当于考古,你不去考,没人给你准备资料。不要说一去几百里几千里,不如在网络上找找省事。是的,现在网络发达,许多资料可以在网络上找到,但是在网络上没有这个。谁给你提供这个?网络上即使有,也不是这个角度这个内容。必须到现场,才可以调查、考证、挖掘出古树所蕴藏的深意,才可以打通采风采访、调查研究所获的内容。你想,一棵几百年几千年的古树摆在那里,你只知道有这么一棵古树,和你站在古树跟前看着这棵古树,是完全不一样的,你在现场和不在现场所发掘的内涵也完全不一样。
现场感受。何况,你是把它当作文学来做,不是单纯的科学研究。如果是单纯考古的话,我也可以委托人把它弄完,或找一个团队弄完就行。我这个是文学,文学必须作家亲自到现场。文学是蕴含感情的写作,你必须去感受,你必须去发现,你必须去发掘。没有身心的投入,你怎么进入创作?没有现场的感受,你怎么写出一种感觉?你不去到现场去感受,怎么会有现场感觉,怎么会有现场融入,怎么会有现场启发?所以我坚持写文章必须要到现场,一定要到现场,看现场的实物,找现场的实感。即使古代的现场已经不存在了,但你去看生态、看环境、看氛围,你受到的现场冲击,就和别人讲给你的现场不一样,就和别人的现场感受不一样,这样才能有你自己的文学。
譬如,我写左公柳,就得去看左公柳,一看,想到当年左宗棠是怎么抬着棺材栽树进新疆的,那个感觉顿时就出来了。所以我说中国一部近代史,居然是由两棵树做标志的,一个是西北高原的左公柳,一个东南沿海的沈公榕。这个沈公榕是怎么发现的?中国近代海军,是从马尾船厂开始的。马尾船厂是建厂先栽树,沈葆桢亲自栽了一棵榕树,就成了马尾船厂的象征。我2016年写这棵树的时候,这棵榕树已经活了150年了。当时,一个作家朋友在那里写报告文学,他就给我打电话,说梁总,马尾船厂要搬家了,但是一棵树搬不走,这个树如果没人保护,就可惜了。朋友知道,我2012年开始写树,到2016年已写了好多树,就说,你赶快来吧,不来就晚了。我去了一看,嚯,这棵树,遥望大海150年,一部中国近代海军史啊!这树里有中国海军的百年历史。
本来,马尾船厂是朝廷要让左宗棠去办的,但左宗棠当时要去西北平定叛乱。晚清时代社会腐败,负责任的大臣不多,朝廷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干这个事,左宗棠想来想去说只有沈葆桢,就推荐了沈葆桢。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,当时正在家里丁忧。左宗棠就动员他,他说我是当地人,当地人关系太复杂,我不干。后来又说,开造船厂,没钱怎么办?左宗棠就帮他贷款,找红顶商人,找到了浙江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来出钱。最后把沈葆桢推上去,他才去西北平叛种树。沈葆桢这个人很有意思,不干则罢,只要干了,没有干不好的。他上任就栽了一棵榕树,这棵榕树,150年,和中国第一个船厂一起成长。所以我说,中国的两棵树,标志着中国的近代史。你不到现场去,绝对发掘不了这个故事,绝对没有这个感觉。因为文学是人学,得挖掘人的思想感情。
李景平:人文森林或生态文学是要追求在场感的,徐霞客在山水间行走多年而有《徐霞客游记》,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住两年而有《瓦尔登湖》,胡冬林在长白山一住五年而有《山林笔记》,李青松在自然奔跑多年而有《万物笔记》,您走南闯北几次历险而有《树梢上的中国》,这应是一种铭心刻骨的生态文学现场的寻找。请谈谈你的故事。
梁衡:徐霞客我写过,他是颠沛流离,奔波一生,才有了《徐霞客游记》。李青松是我的老朋友,他在国家林草部门任职,自然要全国到处都跑。别的作家怎么跑现场,肯定是什么状况都会遇上。我呢,是在黑龙江原始森林里,差点出事。当时是受到了蜱虫的攻击。蜱虫这小东西,会钻进肉里,钻进人的身体,吸血,注射毒素,攻击人的神经系统,危及人的生命。
我去黑龙江的时候,这种虫子,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在当地,每年5月1号开始到7月1号要打防御针,这个期间是高发期。林业工作者都要打,进入森林的人也要打,相当于打疫苗。我去的时候,是6月30号,正好踩在这个线上;他们接待我的人也大意了,也没给我讲这个事。那天从森林里出来,我洗了澡,睡了一晚上,第二天一摸,在脖子这儿,虫子进了肉里,他们吓了一跳,没出林区就赶紧开刀,把虫子取出来。这个虫子取完了,中午回到哈尔滨,住在林业局招待所吃饭,我一摸,腰上又一个虫子在肉